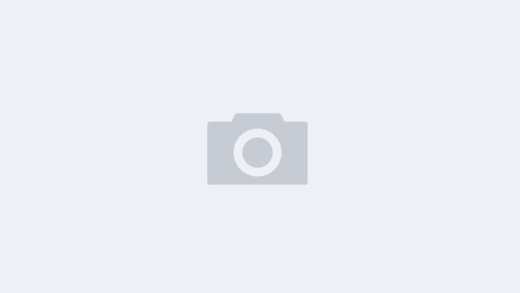不同年龄段对于同一部小说的看法会有着巨大的不同,重读这部书的契机是在米兰昆德拉的溘然长逝,让我有了重读名作的想法。本科的时候曾经看过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反复描述宿命般的“es muss sein?es muss sein! ”,以及对于刻奇,或者说媚俗的共情。但是这种共情是一种虚假的共情,受年龄和见识所限,当时我总是将自己对于集体活动的厌恶做了简单的映射,为自己对于被期望的普遍反应的迟钝做出一种解释,认为自己是一种独特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满。“es muss sein?es muss sein! ”在当时的我看来也不过是宿命之重带来的不思索的轻盈,轮回的形而上学所带来的个人命运之轻。
多年之后的重读,这些想法并没有说完全被推翻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刻奇的理解当然不再仅仅是学校,也有了政府和共产主义政权中的集体主义思考,进而引申为所有泛化的群体内部的情绪和行为规范的刻奇。刻意追求与常人不同本身是否就是对于独立思考这一概念的刻奇?当然,顺着这样的思路只会得到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但至少,不会在葬礼上因为陷入无法自拔的悲伤而自我怀疑。宿命之重,当然有着阿特拉斯顶住天穹的沉重,有着决定是出自自我还是宿命的怀疑,对于他的回答,也必然会是 “es muss sein! “
尼采认为,我们的世界是“永恒轮回”的。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都由无数次的重复。我们的生活是能够被预演的,有朝一日,我们的生活会按照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前者中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们就会向耶稣一样被钉在永恒色十字架上,无法承受的重负将会沉沉的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这样沉重的重负必然会使我们的决策变得轻盈,万物既已无法改变,每一次的轮回不过是事物的简单重复,那么每一次的决定必然会变得轻佻。
对于托马斯而言,轻与重的思考是作为医生这类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恃与天生而来的责任感,和自己想要通过性去探索了解女人的轻佻。是写文章怒斥政府还不如俄狄浦斯般自欺欺人的我不原谅和为了生活丢掉医生身份的沉重对比。也是对特蕾莎宿命般的爱与肉体上不断的背叛。特蕾莎则更多的是一个契子,一个引发人思考灵与肉之间关系的契子,对Tomas的灵魂之爱与肉体上背叛之间的痛苦。不断地剥离肉体的独特性,解构隐私与灵魂的家庭,庸俗化的家庭构成与平静和喜好读书,想要有着不同生活之间的轻重对比。而对于萨宾纳而言,她的轻盈则是不断背叛的生活,背叛成长中的集体主义,背叛被侵略的祖国,背叛真心爱着自己的弗兰兹,对于她而言,背叛已经成为了生活的目的,而背叛的代价也越发沉重。
在向伟大进军这一章节中,昆德拉不无戏谑地记录了他所知道的斯大林之子的死亡。堂堂铁人的儿子,为了不冲厕所盈出的粪便愤而自杀,这一死亡的原因可谓荒诞而出格。但是换而言之,这种死亡终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而死,是为了自己的高贵而亡,比苏德战场上枉死的亿万生命更加沉重。从这里便可看到昆德拉对于轻重之思考。
在最后的卡列宁的微笑章节,昆德拉总算是流露出了难得的温柔,给予了托马斯和特蕾莎一个温馨的结局。卡列宁的死亡并不沉重,而是温馨而又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