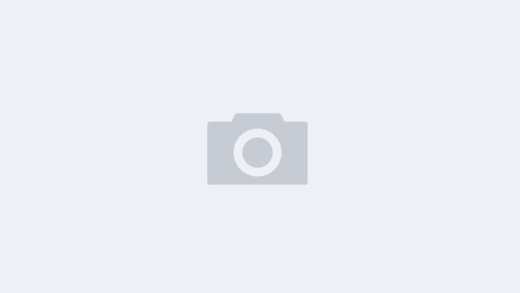跳至内容
在以现代目光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时会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承担行政职责的政府官员的考核方式从最初的考察个人品德的举孝廉到诗词歌赋乃至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从来没有对官员行政能力的考量而是对文学以及道德水平的考量?官吏的殊途分化又是从何而来,为何官员要同时承担行政职责以及教化职责?为什么会有父母官青天大老爷这种将管理者视作父母等血缘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管理/被管理者关系。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回到士大夫政治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传统上,探究为什么不是分化的官员而是一个不器的抽象化的君子承担了实际的统治职责。
阎步克从士这一文字的训诂为起始,探讨士这一阶层在封建制国家中的原初含义,从参与战争的成年男子可以引申出婚配之后的成年部落男性到封建制国家内部的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士本身的含义就是区别于奴隶阶层的统治阶级的成年男性。而在西周封建制逐步崩溃,礼崩乐坏之后,不同仁人志士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同源却又大相径庭的解决方案。出身乐官的孔子提出克己复礼,追求和而不同,抵制社会分工的进一步进行,用君子不器以及仁乐等理念去弥合越来越大的社会分歧,进一步发展了礼乐中亲亲,贤贤,尊尊的看法。而法家则选择了承认社会分化的出现,并选择了尊尊这一路径极致强调行政力量的发展,用一套繁密且细碎的律法规定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集万钟于一身,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了皇帝一人。此处的法制并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法制,所有的法律律令皆出于皇帝一人,本质上仍然是完全且彻底的集权,法律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黄老哲学则全盘否定社会分化的存在,一意孤行想要复古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推崇的则是无德无能的乡贤老人。
但是这三者所给出的回答在不同社会阶段有着不同的回响,对于战争状态下的战国社会而言,拥有者最高行政效率的法家自然是不二的选择,皇帝驾驭作为战争机器的国家如臂使指,一丝一毫的民力均可被高效的管理体系榨取用于战争需求,但显然随着疆域的扩大导致的行政效率下降,以及完全的极权对于统治者的高要求,这一官僚体系并不能无休无止的运行。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道德与礼仪,血缘关系的温存会呼嚎着需求一个更温和的社会。由此汉初的统治者选择休养生息的黄老哲学,但一位的复古并不能适应业已高度分化的社会,行政机器并没有被改造而是仅仅按下了暂停键,当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上台时,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这一现状。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没有使得儒学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显学,各类思潮仍然在潜流中涌动。不管是汉宣帝的外儒内法的王霸之道还是各种儒学官吏的法家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杂糅。这自然也会引起儒生的不满,这一不满情绪发展到最后就是王莽篡汉之时疯狂的反攻倒算。而王莽新政的失败以及东汉的兴起则进一步确立了儒法交织的现状。承担文化职责的学者与承担行政职责的官吏合二为一,成为了传统中国的主流–士大夫。
对于士大夫政治的考量,以现代眼光而看必然是一种社会分化不彻底以及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最佳体现,也是古典中国没能走向现代法治以及科层制社会的最大阻碍。但中古中国并非没有尝试过完全职业化的官僚体系统治,但是在一个未分化的,乡土气质浓厚的农业社会推行的官僚体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反而是所有命令皆出于皇帝一人的极端极权。士大夫的出现本质是对皇权的削弱与分割,是对极权的反抗,是在没有私产以及契约合同下所能提供的统治第三级,维护的是传统社会中广泛分布根据血缘以及朴素道德观的“礼””仁”。不管这一阶层在后续的社会中如何嬗变和皇权媾和,至少在原初时也是带着美好的期许,虽然亲亲贤贤尊尊这一要求与现世社会种种掣肘决定了这一理想必然会变质。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不应该忽略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所带给我们的习俗惯性,而更应该将其改造适应现代这一更加分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