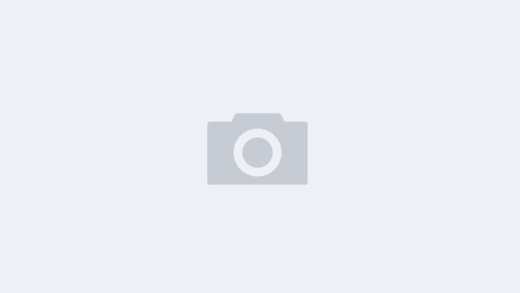研究型的文章和文学型的文章会有着很大的差距,转型中的地方政府是一部典型的学术文章。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些研究型文章通篇的核心观点只有一至两个,而剩下的内容则是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反复去论证。如果是追求新奇,追求多变的风格,那么这类文章必然会让你失望,只有从最开始的新奇到最后感到老生常谈的厌倦。但作为自己写个论文的学渣,这样的论述思路反而会让我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我喜欢看到一个确定的观点,和由这个观点发散出的反复论证,即使最后的结果可能并不正确,但论证的过程会让我感到极其舒适。
文章描述的就是中国的政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交互关系,主要用了关系最密切的财政关系来进一步说明,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协调沟通,地方政府内部同级政府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如何使用政治锦标赛这一手段来协调管理地方政府,保证政策的正常推行。由此进一步分析了当前行政手段上的一些独有中国特色,以及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这些特色如何去解决。
传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管辖有理想的科层制,使用完善规范但同时意味着死板的层层制度约束政府雇员的合法伤害权,在这样的制度下,雇员的行事天然倾向于保守,只要不犯错就是最大的完美,作为民众自然不会感到生活受到了无形之手的干预,但也同时会感受到政府治理的死气沉沉。另外的极端就是完全的外包制,上级政府制定一个财政,行政目标并提供合法的暴力工具给下级政府而不去管理具体事务,这样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的冒进,毕竟交足上面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好处是在恰当的目标激励下地方政府有着充足的动力,但不受约束的权利必然会导致恶意的合法伤害与权力寻租。而中国特色的分权方式就是发包制,将一个个具体的事务打包并分发给各个分级政府。
发包制和雇佣制的区分:资产所有权/激励契约/任务分配三个角度来区分 行政发包制介于两者之间是在行政组织边界之内的”内部发包制“ 基本特点:
- 发包方拥有正式权威和剩余控制权,这不同于纯粹外包制中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平等契约关系。但具体执行全交给承包方。
- 承包方拥有剩余索取权,有强激励
- 行政发包制下,和韦伯式官僚体制不同,法理约束少,主要是绩效导向。为了绩效可以打破法理。
行政发包制的”行政性“主要在于:
- 处于同一个权威体系,发包人具有支配性权力,双方处于不完全契约中
- 承包人具有能够升到上一级发包人的仕途前景。承包人要与其他承包人竞争。
- 承包人面临一定的官僚规则约束和程序控制。
行政性的核心就在于,用官僚制来在政府内部约束发包制可能造成的放大的扭曲和伤害效应。
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约束核心即为人事权,人事权可以用于对于官员失策的惩处,也可以作为官员个人的主要行政激励。利用人事权这个胡萝卜又设计出了官员锦标赛这一天才般的制度。上级政府可以设定各个目标,比如辖域内经济排名,相对于自身经济增长幅度,以及近年来的环境考核指标来对下辖官员进行考核,利用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这也是民间对政府诟病对上而不对下的问题根源。地方政府对其管辖地的公共服务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即百姓不容易获得替代性的服务提供方(除了政府组织的移民以外,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公众在古代不容易跨地域迁移),这相当于增加了地方官员从中央政府可以获得准租金,那么,官员之间政治锦标赛的作用之一以官员之间的竞争替代了百姓流动(“用脚投票”)所引发的蒂伯特( Tiebout)竞争,使官员的政治命运必须依赖于上级政府,限制了地方官员享受的租金规模。而与层层发包的制度相对应,中央庞杂的细分机构对应的基层部门却不可能保持有同等的规模,这便是基层办事人员所吐槽的上面千根线,地方一层针,那么对不同来源的发包任务并会有着不同的取舍以及执行顺序,这也使得地方政府反向对中央政府产生了约束。中央使用的官员锦标赛与实际执行层面的先后顺序,共同拧巴成了现在的执政现状。
当然,这些问题和优势并不是死板一块,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变化。从建国至今,财政以及行政权在收放之间不断平移,既有大规模的分权也有大规模的收权,在威权政治的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乱相,最近一次大规模的变革便是国税和地税的分割,由此导致的房地产以及土地经济狂飙猛进不必多言。政府和资本之间的媾和与纷扰,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都在这个大框架下不断嬗变。
疫情最后一年的政府失能,人心思变以及到最后的政策180°大转弯,这一切的根源可以从这本书里分析一二。制度并不存在好坏,只有其是否可以适应实际的经济社会环境。只要认真阅读,很多当今社会的怪相都会在书中得到解答。
引文:
中国的集权不是体现在财权、人员和事权上,而是在人事权和行政控制权(相机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中国可能又是最分权的国家。这里说的分权,是指行政性分权,即地方政府在执行其职能时实际拥有的决定资源配置和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能力。 属地化的逐级行政发包相当于把复杂和细致的行政管理事务从中央层层发包,按地域逐级分解给下级政府,由此可以大大减少中央政府的事务负担,使得中央政府可以集中于大政方针的制定和监督地方政府的实施。在层层转包的过程中,中间政府成为基层政府的监督者,对中央和上级政府负责;而中央只需要监督控制和激励这些数目不多的中间政府的行为就可以了。 行政逐级发包和财政分成使得中央可以保持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人员和财政支出规模,同时握有最核心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一方面是一个集权国家,另一方面却一直保持非常低的中央行政人员和财政支出的比例。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面临日益复杂的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拥有14亿之众的人口却只有大约3万左右的中央核心公务人员和大约15%的中央财政支出占比。 如果说,地方政府对其管辖地的公共服务具有相当的垄断性,即百姓不容易获得替代性的服务提供方(除了政府组织的移民以外,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公众在古代不容易跨地域迁移),这相当于增加了地方官员从中央政府可以获得准租金,那么,官员之间政治锦标赛的作用之一以官员之间的竞争替代了百姓流动(“用脚投票”)所引发的蒂伯特( Tiebout)竞争,使官员的政治命运必须依赖于上级政府,限制了地方官员享受的租金规模。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便不难发现,中国的政府治理是在从计划时期的集权体制全方位向传统行政体制回归,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80年代初期开始的行政性分权把原来集中在中央一级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大规模下放给省级政府,省级政府也依次向下级政府下放权力,这些重要的变化事实上使得政府间关系更接近于传统的行政发包体制,形成了地方高度分权的体制。第二,财政包干制秉承了传统上的财政分成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使之拥有重要的剩余索取权,并更为自主地支配其财政支出,尤其是预算外资金给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第三,在政治锦标赛方面,考核地方官员的标准从过去的政治忠诚和政治素质转变为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把官员自身的利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利益紧密相连,而人事控制权从以前的“下管两级”转变成“下管一级”则让省级政府可以在省区范围内逐级推行政治锦标赛,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奠定了一个激励兼容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分权、财政分成和晋升竞争这三方面的改革不是孤立的改革,它们事实上相互支持、相互加强而构成一个内在一致的地方政府治理的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