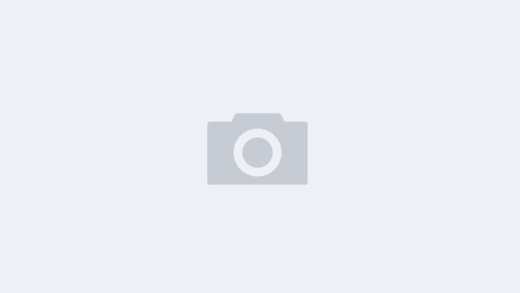-
惨败是莱姆在冷战高峰期所写作的一部不算著名但却同样引人深思的作品。故事整体有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前半段是400年前机甲驾驶员在土星著名卫星泰坦上前赴后继地营救陷落在拥有着移动间歇地下喷泉的伯纳林姆并相继遇难,后半段是400年后科技大规模发展进步之后,探索舰船欧律狄刻号上船员在道德困境下随机复活了遇难人员中的一位,并在亚光速下航行至最有可能拥有着类人生命的昆塔星上尝试与宇宙生命达成初步接触。然而昆塔星上的生命并不是人类所设想的理性与和平的生命形式,而是出于对立与不断猜忌中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下的星球,多次有好的交流尝试被拒绝。在绝对武力加持下的人类认为这是一种无理行为并给出了最后通牒。负责交流与试探的复活飞行员在想要交流的执念下忘记了发送生命维持信号招致了母舰的致死打击。讽刺的却是在打击来临的瞬间,飞行员在真正理解昆塔星“人类”的本来面貌。
文章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叙述中心,甚至可以称得上单薄与无趣,泰坦星上的故事仅有救援的推进,而昆塔星的生命形式则是小说后半段的核心。在故事情节的编排上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层层递进引人入胜,反而掺杂了众多的哲学思辨。小说的核心构想有两个,一个就是与索拉里斯星如出一辙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讽,另外一个就是对冷战期间美苏对立的政治军事形态以及对于生命本身发展的思考。前半部分的隐喻非常之多,并有着相当数量的用典,只有了解了俄耳普斯与欧律狄刻的故事才能看出其中的精妙。探索外星的母舰名字就是欧律狄刻,放出的探索舰船则名为俄耳普斯,昆塔星系的中心黑洞则是冥王哈迪斯,搅动黑洞的探针则是飞毛腿赫耳墨斯。俄耳普斯上的船员所秉持的也如故事中一样,不要回头望向母舰。而故事开始的泰坦则也是希腊神话的起源。
人类中心主义是莱姆一直批判着的一种思潮,与索拉里斯星中的内核完全一致。人类总是傲慢地认为所有的智慧生命有着相近的生命形态以及智慧,武断地以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所有智慧生命必须经历的,并根据浅薄的知识去预测不同智慧生命在不同阶段所拥有着的思辨。由此,与外星智慧生命的第三类接触必然是可行的,并且任意智慧生命都是友善可沟通可交流的。但是广袤的宇宙显然不会允许这样的傲慢,昆塔星上的原住民显然并不符合人类的预测。由此引出了第二个核心的议题,那就是对美苏冷战期间的猜疑链和不断加码的军备竞赛的反思以及原因讨论与思考。昆塔星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而是由不断猜疑对抗的两个或者多个集团。不管是行星赤道上的冰环亦或是同步轨道上随处可见的拥有着极高科技水平的自卫或者攻击卫星,甚至于在唯一卫星月球上也遍布着巨大武器的遗骸。多个政府间最开始的不信任并不是无法弥合的裂痕,然而在平衡的实力,无效的沟通和剑拔弩张的军备竞赛下,无人敢轻易放松戒备,只能不断加码军备,与冷战的境况如出一辙,然而不幸的是在昆塔星上并没有倒下的苏联,而是不断地层层加码,直到所有的智慧生命均无法承受这样的开支。俄耳浦斯上的舰员在这样的前提下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去与这样的生命沟通,面对如此的恶意是否应该展示自己的雷霆之威?人类自诩为和平,为了沟通与接触而来,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所有的善意均是建立在人类所拥有的军事力量远远大于昆塔星生命的前提之上。在面临一而再再而三的受挫与敌意之后,人类用武力胁迫昆塔星人同意飞船的降落与沟通,却因为自身的傲慢丝毫没有意识到昆塔星人并没有人类的外表,进而给予了对方无穷的毁灭。目光回移,这时候再次回想泰坦星上拥有着人类所能理解外表的二氧化碳雪雕却是不折不扣的无极生命,智慧生命一定会拥有着类似的外表吗,或者说拥有着相似外表的物体一定有着相似的内核吗?
莱姆可以说是硬科幻的代表,笔力冷峻而一板一眼。泰坦星上巨大的机甲并不是空有一个躯壳,还是有着巨大的液压传动机构,动力来源则是现金人类梦寐以求的核聚变炉,这个巨大的机体有惯性,符合物理定律,会因为操作者的鲁莽而陷入绝境。写欧律狄克飞船时完全不存在的气动外形,拨动黑洞制造时间悖论时的举重若轻。昆塔星上的巨大冰环如何制造,又如何并不符合工程学原理。每一个技术细节并不会因为读者的不求甚解和放松追求而是一板一眼客观冷静地描述出所有细节,或许这些描写对于故事情节并没有特别的作用,但对世界观的建立却大有裨益。也让小说的哲学思辨更加真实。